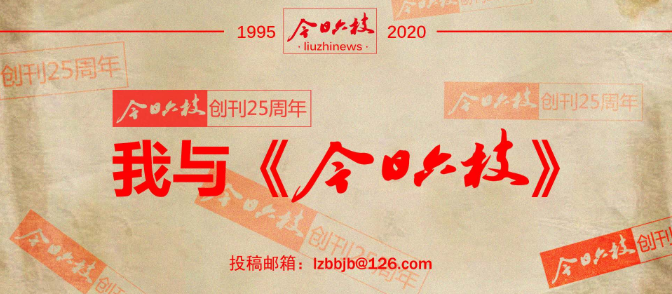
【情缘】人的一生,无不是一次一次地相聚与离散。人们面对着走来,相聚在一起,又背对着远去,渐渐疏离。每一次相聚,都是一次美好;每一次离散,也都是那么让人怀念和伤感。原来的《六枝特区报》如今叫《今日六枝》,叫什么都只是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背后,是一群人默默无闻的奉献,是他们“得失寸心知”的坚守。
1995年10月,我从牛场中学改行到乡政府办公室任秘书,兼做共青团工作。因为经常在市委机关报《六盘水报》发表“小豆腐块”类的新闻报道,被新成立的六枝特区党委机关报《六枝特区报》总编吕选俊老兄看中,通过他的努力协调,1996年4月,一纸函件,我就被借调到了六枝特区报社工作。
从业余爱好一下子变成了工作饭碗,这个弯转得太大。业余的时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投的稿件编辑会修改,实在没写好,编辑就弃之不用。但作为职业记者,每一次采访后,你必须完成稿件的撰写。报社人少,没有专门的编辑人员,大家都是一边采写一边删改稿件然后划版。作为编辑人员,你还要学会修改别人稿件。
说实话,以当时我的文字功力,每一次采访回来,连稿件怎么写都愁眉苦脸,连字词句也不是很通顺。要端好这碗饭,实在太难。好在总编吕选俊,还有两位副总编杨朝荣和卢俊,基本是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常规新闻稿的写法,如何抓住报道要领。
那时,划版用的是印刷厂特制的坐标纸,编辑必须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地数。一个圆圈代表一个字格,字数多了不行,少了又要开天窗。必须精确地计算标题占多少字格,正文有多少字格。因此,划好版面,送到印刷厂后,报社还必须派人守在捡字工人身边,字少的时候,就想法补点;字多的时候,又想法删点。

排版清样出来,还要再次校对,尽量不要出错。校对这活,干多了,总觉得跟小时候在大山里那些石旮旯里去寻找低头吃草的老水牛一样难。那水牛背跟石头完全一样颜色,也几乎一个造型,要准确地找到那一动不动的老水牛,实在不容易。校对的时候,还不能走神,否则用错的字就从眼皮底下悄悄溜走。
在报社干了一年时间,基本掌握了新闻稿件的一般套路,熟练了划版时数坐标纸的工作;在修改别人稿件时,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十来个人的报社,经常加班加点,大家相处得如同兄弟姐妹。
可喜的是,时不时有些稿费收入,可以在羊肉粉馆里大大方方地来个“大碗加”。正干得顺风顺水,一篇《六枝北部烟乡走笔》的通讯发表在刚刚扩版为对开大报的《六盘水日报》头版报眼位置,被时任县委书记看中,就让党办的领导来考察。当时心里没底,家人们更是担心,说什么“伴君伴虎”的。我不知道县委书记那么大的官,我能不能服务好,就惴惴不安地给吕总编说,我去县委办试一个月,感觉不行,还得回报社来。吕总编宽容地笑笑,点头答应。
这样一离开,再回来时,早已物是人非。
十六年后,我转换了好几个工作岗位。在那些岗位上,我感觉身心疲惫,十分压抑,就向组织申请改任了非领导职位,轻松地度过了两年“睡觉睡到手抽筋,数钱数到自然醒”的休闲时光。那一日,宣传部副部长李万军同志见到我,笑着说,要办六枝报,觉得还是请我这个老哥来“提桶桶”比较适合。
我想,六枝能够干这活的人多得是,我都改非了两年多,再混两年多,30年工龄一到,即可申请退休,继续过自己的舒心日子。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第二日,时任宣传部长的幸雪梅同志打来电话,嘘寒问暖过后,让我有空到她办公室“聊聊”。在她办公室,她又提出请我“提桶桶”的事。我有些心动,于是说,老妹,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再一日,一个偶然机会见到县委主要领导,他说县委想办报纸,问我能不能干。
我立即就到六枝宣传部报到。
筹办报纸的人选,都挑选得差不多了,征求我意见后就定下来。幸部长问能不能元旦就出报?只有一个月时间,从各单位借来的人中,虽然都能写点文章,但几乎都没有编辑报纸的经验。
不会就学。我带着兄弟伙,到邻县的新闻中心学习。这个县的报纸按政策停办时,并没有像我们县报社一样撤销,而是将报社改成了新闻中心,继续编辑出版党委主管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新闻中心运作一直到现在。学习归来,我们立即着手装修办公室,购置电脑、学习排版知识,申办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等。
2013年12月28日,元旦刊《六枝》的电脑排版电子版本出来,交由一家公司负责印刷,却因对接出了问题,原定在贵阳印刷的报纸,只好协调到毕节印。因为是第一次编排,或者是其它方面的原因,印出来的报纸各个版面尺寸都不协调,可谓惨不忍睹。不管怎样,总算在元旦这天如期出刊,也算完成任务。 后来,电脑编排技术逐渐娴熟,报纸编辑得越来越美观,印刷也由贵州日报印刷厂代为印刷。让人提心吊胆的是报纸的内容,审稿与校对就成了头等大事。为了不出差错,打出的样报,你看了我看,我看了他又看,直到确认无误,才发送到印刷厂付印。报纸是周报,对开大报。
每到周五,我们通常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但周一拿到报纸,却总发现还有不如意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一多,同事们就自我安慰,自嘲说办报纸是“遗憾的艺术”。

时任《六枝报》总编的龙尚国率记者深入北部库区采访 2014年6月,作为六枝司法局主任科员、临时主持报纸《六枝》编辑业务的我,被任命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继续主持报社工作。到年底,感觉到精力实在不济,就调整由副部长李万军同志负责报纸业务。
虽然不再从事报纸的编辑出版,但对这张报纸充满感情,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爱都爱不够。只要报纸一出来,就赶紧阅读,几乎不遗漏每一个字。直到现在,有机会得到报纸,我都会很认真地阅读,如果发现一些问题,也及时给他们反馈我的想法。
两次县报工作经历,为我文字的提升奠定了基础。还记得曾经与周安贵、李恒一起,为了一个“的”字是留还是删,争得面红耳赤。
第一次进报社时的同事张云英、刘兰、李桂婷、何天霞等人,随着六枝特区报社这个机构的撤销,他们分别被安置在县直机关其他单位。现在偶然碰面,依然感到十分亲切。
第二次县报的同事们,有的还在宣传部坚守,有的已经调离,我也于2015年底离开了六枝。见一面很难,但一见到,与曾经的同事们的那股亲切劲便从心底涌出。
人的一生,无不是一次一次地相聚与离散。人们面对着走来,相聚在一起,又背对着远去,渐渐疏离。每一次相聚,都是一次美好;每一次离散,也都是那么让人怀念和伤感。原来的《六枝特区报》如今叫《今日六枝》,叫什么都只是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背后,是一群人默默无闻的奉献,是他们“得失寸心知”的坚守。 作者:龙尚国 编辑:令狐荣骏 执行监制:何勇 总监制:吴国琴 卢泉





